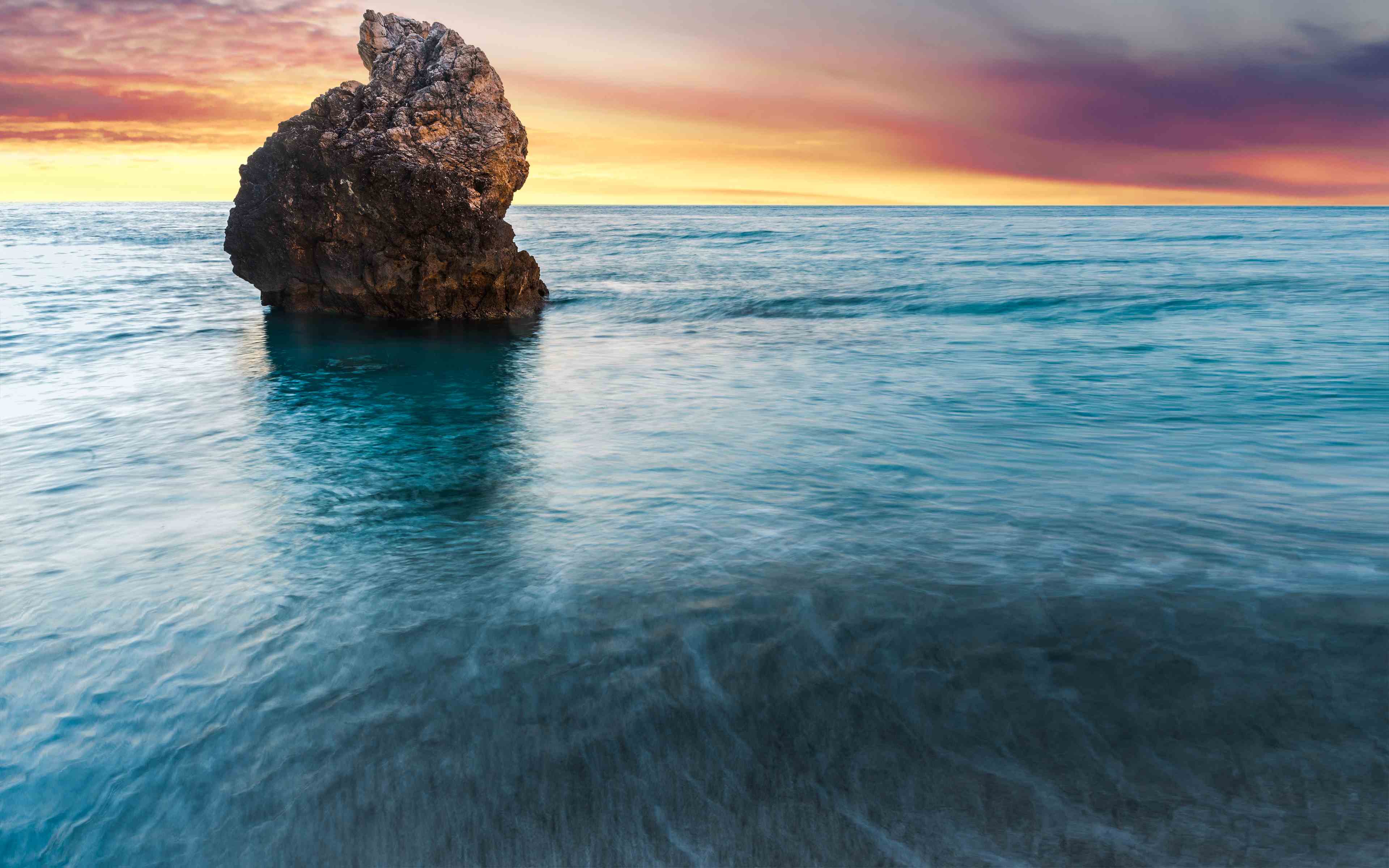叶圣陶先生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新中国语文教育的奠基者,与吕叔湘、张志公一起被尊称为“语文三老”。叶圣陶先生投身教育工作70余载,他的“五论”(学生本位论、生活本源论、实践本体论、习惯本旨论、工具本质论)教育思想源自实践、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叶老留下的许多教育名言被广为引用,今天看来,对于推动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叶老还有一句话影响很大,那就是“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一些语文教师或教学研究者常引用这句话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但笔者发现,有些人对叶老这句话存在误解甚至曲解,与叶老的原意往往背道而驰。
叶老当过中小学语文教师,也当过大学语文教师,新中国成立之前与之后累计编写过17套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绝非叶老一时心血来潮之语,而是他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据查证,早在1945年,针对当时语文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叶老在《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一文中正式提出“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的说法。1978年3月,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叶老在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发言中指出:“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现在大家普遍引述的语文教材“例子”说,主要起源于此。
叶老当时的讲话是对十年动荡给语文教育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拨乱反正。抛开特殊的时代背景,今天,站在新一轮课程教学改革的角度,我们该如何理解“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这句话?
深刻认识“例子”的作用和价值
“无非”亦即“不外乎”“只不过……罢了”的意思。从字面意义和日常语言表达习惯出发,一些人由此得出教材不重要的结论,从而轻慢教材、忽视教材,认为教材“可有可无”,教师在教学时“可用可不用”。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叶老自己对这句话的内涵有明确界定:这是“说语文教本的性质跟作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83页)。说教材是例子,绝不是指对待语文教材的态度。
我们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时会发现,这些学科教材的编写逻辑,总体上是演绎式的(当然,在导入某些知识、讲到某些知识的形成时也会用到归纳的思维方法),以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为统率,依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分章节展开。在这些学科的教材、教学中,也有很多“例子”,但这些“例子”的主要作用,一是帮助加深对某个概念、定理、公式的理解,二是应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相应的问题。而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逻辑是归纳性的,需要教师和学生通过一个个“例子”,也就是一篇篇课文,去学习、思考、总结出一些语文学科的知识来。因此,语文学科的“例子”(课文),是语文知识的“载体”,是学习的“凭借”,离开了这些“例子”,语文学习就无从谈起。由此观之,语文教材的“例子”,其功能、作用和价值,比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学科教材中的例子(举例、例题)大得多,二者不可相提并论。
有人可能会说,为何中小学语文不能像其他学科一样,基于学科的系统性和概念体系进行内容分解,按照章节和知识的逻辑体系来编排呢?笔者想这个问题包括“语文三老”在内的众多教育专家肯定都曾想过,但是自语文学科诞生百余年来,每册语文课本由若干篇课文组成的体例沿用至今未变,定然有其道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方面的语文知识,需要学生依托具体的载体和情境去体会、感悟,由“一”而“三”,由感性认知到理性总结。知识隐于课文中,这不仅是由语文学科独特的性质、地位、功能和学习方式决定的,也是顺应儿童青少年母语学习思维发展规律的要求。
体会“例子”选取背后多方面的考量
对“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的另一大误解是认为语文教材的选文具有随意性——既然课文只是“例子”,用哪个“例子”不用哪个“例子”,有那么重要吗?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语文教材的选文高度关注,中小学课本中多了哪篇文章、少了哪篇文章,往往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乃至引发争议。这种现象充分说明,语文教材选文兹事体大,绝不可凭个人的偏好率性而为。
多年来,语文教材的选文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一些经典篇目数十年来在教材中极少缺席,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但每次教材修订,选文总会有所增删。这种增或删,绝对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十分全面而深刻的考量。
笔者认为,“例子”的选择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的情况:首先,要考虑到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具有体现国家意志的性质,应站在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高度看问题。以2017年开始使用的义务教育统编语文教材为例,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渗透”,在选文上,一是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教材中古诗文方面的内容有较大比例的增加;二是加强了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经典篇目;三是加强了国家主权意识教育的内容,增加了一些相关篇目。
其次,要考虑文章自身的“品质”,按照统编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要“文质兼美”,“选文既要突出经典性,又要兼顾时代性,还要重视选择思想格调高、语言形式美、值得诵读涵泳的作品,强调体裁的多样性,涵盖古今中外各种文体。”要达到上述目标,需要广泛征求各领域专家的意见,论证课文内容的准确性和历史真实性,以及是否符合科学常识,经过反复讨论、斟酌,最后才能定下来。
再其次,要考虑学生的思维发展规律及不同年龄阶段的接受情况,一篇课文多长、生字量多少合适,牵涉哪些语文知识,都需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某一篇文章,放在五年级可能很好,放在三年级学生难以理解,就不合适了。
由此可见,教材中的每一个“例子”都不是随意选入的,更不能随意更换。
用好例子,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
叶老“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这句话,当时主要是针对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教材至上论”的,那就是拘泥于教材、死啃书本,以为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把课文涉及的知识点讲全讲透,语文学习就达到目的了。这样的弊病,在经历多轮课改后的今天依然广泛存在。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例子”、用好“例子”?按照叶老的说法,教材只是“举一隅”,希望学生能学得方法,养成习惯,“以三隅反”。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教师从“教教材”走向“用教材教”。
教材是依托,是凭借,但不是语文学习的全部。语文是母语教育,语文教育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承载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使命。因此,语文学习必须通过“举一反三”,学一例而知一类,由语文课本走向更广阔的语文天地。
要重视教材、吃透教材而又不拘泥于教材、超越教材,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在教课本上的“一”时,自己脑子里要先有“三”,也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视野,要提前准备好与某篇课文相关联的学习资源。这和我们日常说的“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是一个意思。
由此,笔者想到课程周刊版面上开设的“读统编语文 品传统文化”这个栏目。开设这个栏目,是想让语文教师分享讲授涉及传统文化的课文时的经验和感悟,但遗憾的是,多数教师写的稿件并不符合要求。很多文章的前半截——“读统编语文”写得“很到位”,以至于写成了对某首古诗词或某篇文言文逐字逐句的“精讲”,但由此扩展延伸出去的部分——“品传统文化”,却没有写出来或仅寥寥数语、浅尝辄止。而实际上,后半截才是落脚点。
当然也有写得非常棒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主任朱于国就是其中一位。比如他在写到小学一年级的识字课“天 地 人”时,从简单的三个字,讲到古人对天、地、人的认识,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又比如他把教材中与数字有关的古诗词整合起来,让学生体会中国古代诗词妙用数字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他把小学语文教材中写秋天的13首诗词联系起来对比分析,让人看到同样是秋天,在诗人笔下却呈现出或悲愁伤感、或明艳高洁等截然不同的意境,品味秋之人生诗意。还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小语室的杨祎老师,她在详解苏轼的《题西林壁》时,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诗,扩展到对宋诗“哲思”特点的分析。语文教师在教学时,也应这样由此及彼、纵横联系、拓展延伸,只有这样才能既充分用好“例子”又不囿于“例子”,让学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才能以“例子”为跳板,带领学生走向更深更广的文化世界。
从“教教材”走向“用教材教”,还包含一层意思,那就是要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的认知从低阶的死记硬背转向高阶的迁移应用。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在教学方式上注重启发、激发,而不是越俎代庖“满堂灌”。唯有如此,才能如叶老所说——“把知识化为自己的血肉”“化为自己的实践”。而这,不正是当下所倡导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吗?
(作者系本报记者)
《中国教育报》2021年07月30日第3版
作者:汪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