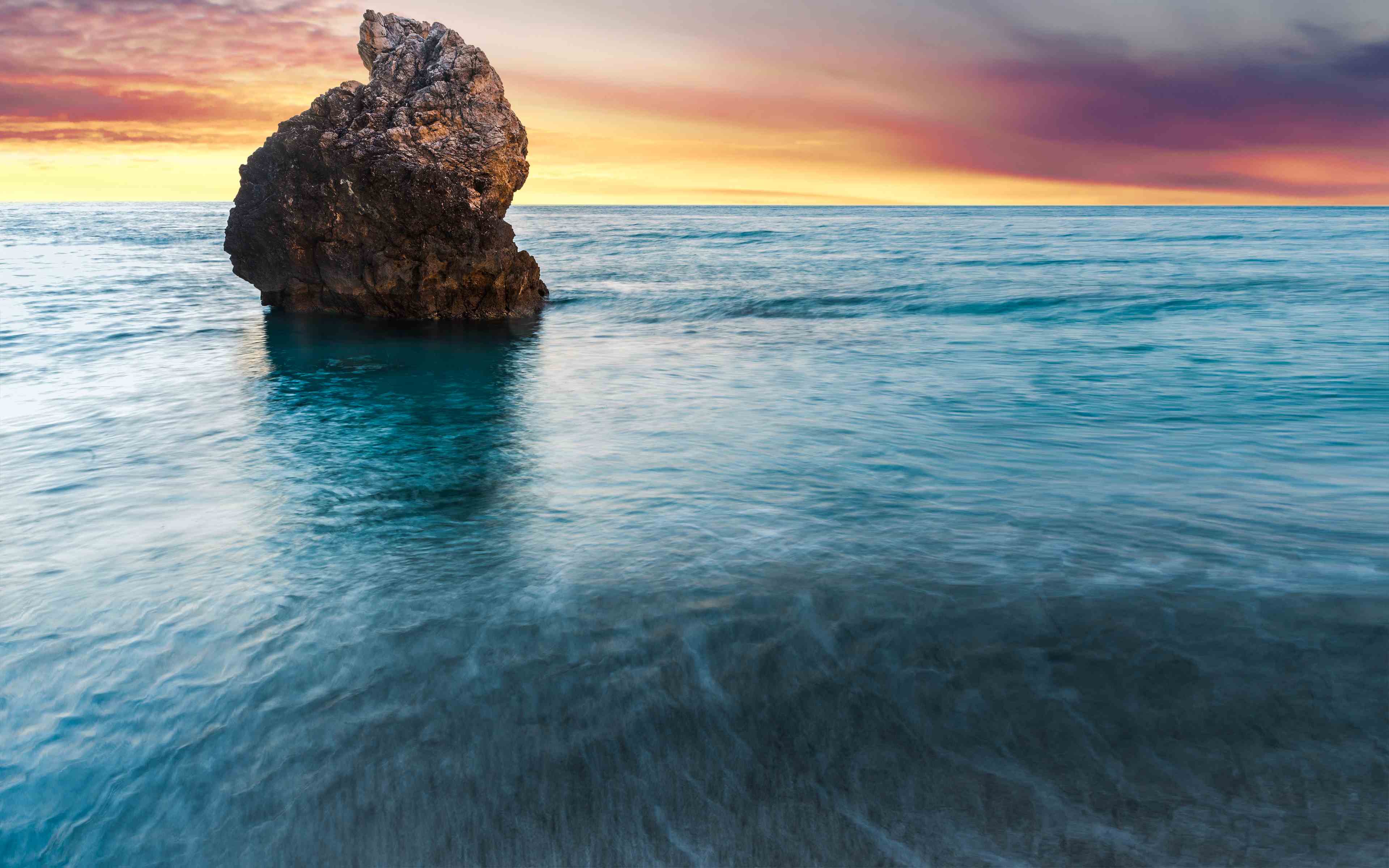牧场小说(长篇小说连载(123)《农场?下卷》(作者刘灵))
小儿麻痹症患者任煜一幅心痛的样子摇头晃脑。突然,他感觉整个人情绪都不是那么好,谈得上谁糊弄谁呀,都他妈是自己在糊弄自己哟。那样子贪杯,肝脏、肠子还会有不烂的道理才是怪。也明白自己只不过是想在酒精液体里求得种虚假安慰。
“真的能变得更宽心,更活得洒脱,肯定特别困难。我从来都不信这个。”
“你俩别用这种眼光盯着我,别人不了解,好像我偷了你东西似的。”
“就是,让人周身不舒服。”
“迟早叫你站着走不出二门岗。”
“确实,我没偷喝酒。”
又是万籁俱寂的慢慢长夜,有些人扯鼾,有的人屙屁,还有人梦呓,至少,三张床上有人正在打飞机,其中有一个家伙还干了两回,也想不通他们精力怎么那么好呢。那个爱梦游的同学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拉开门溜了出去。从前还有人想拦他,但怕把他当真吓死,现在连大队和中队值班,包括室长都早习惯了,也不管他。他醒来后从不知道自个儿干过什么,也幸好,关在四合院找不到坟包给这狗日的刨,还不至于掀开棺材盖啃尸体,犯下辱尸罪。反正,他没想过把大围墙打穿。
“也不会爬上去割电线。”白桦对大队付说,“我没发现这举动。有当然制止。”
何况,他手上并没有任何作案工具,弄伤的也往往是自己,都是些小伤。他又该仔细把伤口舔一舔了,还是尽可能保持低调,别到处声张的好。默不作声最完美,太想改变些什么,欲速则不达,又叫心急吃不成热豆腐。他妈的,尽光想些好事情,快两年没尝过豆腐的味道啦!想变成自己长期以来希望的那种人,到底期待成为那种人也是迷糊的。其实连自个儿真的是不明了,五岁的时候生病发烧,留下了后遗症,这种可耻的缺陷让他再三成为小伙伴们嘲笑的对象。又因为恼羞成怒,每次就想杀个把人来扯平,这种念头,由来已久。他好像是偷自行车被送劳教的。
说起来也真他妈王八蛋,狗屎运气差劲,有点想不通。自己又不能骑偷辆自行车来干啥?害怕最终会越滑倒越爬不起来,成为连自己都讨厌的那种人。任煜可是比任何人都更能体会滑倒在道路上,特别是滑倒在水洼烂泥浆里,拼老命撑了多次,始终爬不起来那种滋味。天空光线里呈现出烟灰色,空气中尘埃无声无息在旋转,飞过来朝他的脑门顶撞。也就是说,连硬壳甲虫好像都敢欺负他,仿佛觉得这一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那种内心深处的悲哀,绝望的心情,不用仔细考虑,任煜肯定比哪个都体会得更深,痛苦到脑袋要炸裂。
对他来说确实不公平。人生的路本来就窄,偏偏还挑选了一条更窄,几乎就是走不通的路……那个害惨了自己的家伙,他现在躲在哪里?更准确说,任煜没想到要去偷自行车,他只是替人把风。他又不会骑,偷来怎么可能扛得走,那些公安也不用脑子想好,就轻率定了罪。其实有许多事情,就算用脚趾头也能够想清楚。
狗娘养的就是些大笨蛋。
他并不是现如今遭罪了在打反悔。
“被关在四合院,像是圈养一头猪那样,又管吃又管睡,事实上的确蛮不错。”
“猪到头来,会挨上一刀。”
“那种是指死刑犯。”
“确实是,你运气还挺好。”
“这种比喻太有问题。”杨军争辩说。
“真的是不恰当,又不怎么吉利。”李刿气呼呼帮腔说,“我总之觉得,这种屁话听起来,不光不吉利,还特别刺耳。”
“如果不再继续犯事,你就能够平安渡过这条河。”任煜挺有点儿文艺细胞,用他们都不大听得懂的用词习惯对同学说。
“是三年,”李刿把自己鼻尖的粉刺挤破了。“我可能三年都看不到那条河。”
“好像,”杨军说,“你巴望能够在这个农场呆上一辈子。”
他点了点头。有件小事任煜从来没告诉过哪个,也就是,连杨军和李刿都没对他俩说,怕被他们没完没了大骂傻,直杠杠冒傻气,脑袋瓜给门板夹坏,扯奶疯,他俩一向习惯了,哪句话不恶毒不骂哪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小儿麻痹症患者任煜本来不会送劳教,他事先和人商量好,愿意替人顶缸,把好多责任都平白无故揽到了自己的头上,对方拿两百块钱,由他亲手交给奶奶用于生活。父母在他三岁那年离婚,母亲还因为拐卖儿童罪判死缓,所以他当初生病没人管,奶奶的年龄太大了。那家伙还答应每个月负责通过邮局寄二十块钱给任煜,钱总是一次不拉汇到四合院干部又换成了牛皮纸给他。彼此都还能守信用。他把这个班房其实坐得有滋有味,就像是坐花园。这种事情,他不能够说漏嘴,也就是说他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讲,事先有口头协议,男子汉吐一口唾沫就能砸出个坑。甚至连当地某个派出所的所长(对方的亲舅舅)也知道,任煜说话是作数的,都不需要双方签什么字,画什么押,更用不着按红泥指拇印。所长只是明确地说了一句,必须的程序总之得走。
他在四合院最好两个朋友从内心当真猜到了,任煜其实并没有犯哪样严重事情。
“管他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老话说大马过得江,小马过得河。”任煜笑起来,“只要不拉上法场枪毙就成啊。”
“我保证你不会。”对方拍胸脯告诉他。
“就是要理个明白,不敢稀里糊涂。”他说,“更得搞清楚,你讲的不是酒话。”
“就是嘛,这种好事哪里找。”对方说。
他想起自己仰脸凝望着那沓钱,反而一副讨好的样子……任煜揣好钱,转身朝家的那一条冷清深巷子走去。
街上,闪耀着路灯的片片桔红色斑点。
杨军长期以来觉得用不着太伤感了。他初中毕业那年终于想谈恋爱,热火朝天半个学期又让第二个人端飞碗,简直是把脸丢尽了。凝望着沉甸甸的夜色,他十分恐惧听到从任何人的嘴里说出那种绝情话。他拿水果刀把对方肚皮划开一条寸把长的口子。像83年那种情况他差点被判了死刑,幸亏老师以及同学家长包括伤者本人都在法庭上开口帮他求情。“说吧!”他让人弄不大明白地耸了耸双肩。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冷静。”杨军说。
“那就好,只怕你还继续大白天做梦。”
李刿打个饱嗝,接着想吐,到底忍住了。
“好像是这样子,我曾经好几次想要那两个狗男女的命,但是手抖,心又虚,没料到,他全家反而帮了我的大忙。差不多等于是救我条命。我也长时间迷迷糊糊,究竟恨不恨他们呢,我俩本来就是邻居,从来都没有仇恨。我不可能像杀死只鸡那样杀死个把人吧。不错,我把他杀了一刀,结果,又背起他打车往医院里送。”
“可耻的是那个女的……你现在最痛恨的人,可能是骗你的姑娘。说得对不对?”
“不知道……现在,甚至还有些想了。”
“真他妈太没出息了。”
“你们说说,搞不懂,他们全家人为什么反而要竭尽全力救我。不像装样子的。”
“恐怕是担心你有一天从牢里头出去会破罐子破摔,反正都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找他全家人报仇,这事不是从没发生过。”
“你这种说法不对,落井下石的话,当时把我枪毙了不更一劳永逸,万事大吉。”
“万一你没判死刑呢?毕竟没有把握。”
“好像是,说得也有点道理。”
“可以考虑他们良心发现。”
“恐怕也是老天爷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我心里边确实是爱过她的,而且,这样的爱情即使到现如今都很难抛开。”
同学们在宿舍陷进了长时间沉思。李刿也是有过不简单一段轰轰烈烈爱情经历的,而现在,很明显也是不可能的了。接到家里来信说,那个姑娘去年的年底已经结婚,哪怕自己再怎么嫉妒加恨,也是鞭长莫及。嫁作人妇的前女友3月份都生了一个女孩,你别说,小娃娃照片上看跟李刿小时候还长得特别像,最相似的地方是鼻子,这可当真是一场莫大的讽刺戏。他们未免太想当然了,内情也只有李刿自个儿最清楚,他其实跟那姑娘根本就没发生过关系。他传染了梅毒好些年,接近挨抓的头一年又突然出现阳萎。他的这些委屈肯定找不到四合院哪个同学可以倾诉,便借酒解愁。那种带着表演性质的爱情更像是装出来给人看的小把戏。
杨军没本事杀死他的那个邻居,如此一来情况反而更糟糕,使自身受到极大伤害,如果反过来说,差不多就是把自己给杀死了。他怀疑这可能是心死了。“哀莫大于心死。”同宿舍的同学多嘴多舌说。他好像是掉进了猎人陷阱,再也摆脱不掉头顶那团阴影,而那名猎人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对于我现在这种处境来说,真正判了死刑,恐怕情况更好些。不容易毛焦火辣,我其实特别矛盾。”他说,“那些从不关心我的人,偏偏想我活着受罪。”
“好端端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还烦。”李刿嘟哝说,“那你们这样害怕我会死。”
所以才觉得四合院没有哪个不感到矛盾。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你非得好好儿活下去。”任煜大声舞气说,“比起我来,你俩全都有更加充足活的理由。”
周围好几个同学吃惊地朝他们三人打量。
“这个得看上帝的意思。”
杨军叹了口气说。
死亡的诱惑从娘胎里带来的时候其实就强大得不得了,就仿佛在精神和肉体四周布下的天罗地网,黑寡妇瞪着它仇视一切的眼睛。“假如说,精神也同样有什么形状的话。”他笑了起来,拼命把烟吞进肚子去,当场呛着了。“蜘蛛会毫不客气猛扑上去,把猎物血吸干,光剩张皮摊在轮状网上。”他阴森森说。
他的笑声使人听起来起鸡皮疙瘩,像被铁沙子打伤了的鸟叫。
绰号叫鬼鸮的卓欣如是白鼻子。
钟征说又叫白癜风。
“所以啊,”他说,“你不得不承受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嘴巴里比咬破了猪苦胆还苦呢。”
“确实是苦不堪言。”
“也就是比直接死还要难受得多一种痛。”
“你们别老这样尽扯死啊死的,让人烦透了。他妈真的是想死,办法多得要命。”
“哦哟,你可别激我!”
“哈哈,关我的屁事。”
“你他妈脚也不洗。老是爱抠脚丫子,简直比粪坑都臭。”
“快看,大家快点看,窗框上飞来一只紫红色大蝴蝶。”
“明明就是麻黑色的啊!”
“喔,怀疑你是色盲。”
“只要不是花痴就不用麻烦。”
“他妈xx大得像乌梢蛇,连狐狸精都可能会害怕。”
“未必你当真怕捅爆了喉咙。”
“我呸!操你妈。”
骂人的橄榄头在上铺朝地下恶狠狠吐了口浓痰,对面睡下铺的虎头虎脑同学大声舞气骂他别到处乱屙。
“我爱死你啰!”第一个同学用娘们的细嗓音拖声卖气唱似的说。
大家齐声叫喊他快点闭嘴,赶紧闭上臭嘴吧,还有人用手巴掌拍打铁床的铁管。哪个放了个哑屁,下铺有同学掀开蚊帐一角,说他把臭气驱赶出来。另外那个人乐呵呵尖叫:“我可不要你爱。”
“舔我的屁x还差不多。”
“同学们,同学们,来收拾假姑娘啊!”
“懂了吗?根本不需要。”
“现实想改变起来太难了。彼此还是需要爱的,毕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恐怕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感哟。”
“哎哟,我心里边爱着你的呀,好兄弟。”
“你他妈少扯疯!”
靠窗子睡在卓欣如对面下铺叫温荣平的家伙躲蚊帐里面一本正经唱起歌来: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四合院里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吉他
唱起了姑娘爱听的歌谣)
在这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方,终于有了把全部身外之物通通放下的古怪想法。原来,放弃并不是成天在心里祈祷,默念咒语也全部没用,好像得找到一种替代。那就真的必须想方设法去寻找到那个值得自己爱上的人。晚上时间太迟了去吃夜宵,喝烂醉,随便找看不顺眼的小伙打架……关起来未免无聊,闲着老不开心。
好像连骨节骨缝他妈都在咔咔响着。
“哦哟,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不会是小儿麻痹症。”
“当心乱放屁得罪人哦,二中队任煜他们三兄弟找你麻烦,打得你满地找牙。”
“到底什么情况?”
“我谅他们不敢。”他马上改口说,“那就当他是脑瘫。这小伙十九岁才不屙尿放床,会不会复发还很难说。”
“有谁能够帮得上他的忙。”
“这本身就是天命。”
“这家伙对这社会恨之入骨,能够出去的话,就会放把火,找个井投毒。”
“他就是一个天生的变态狂。”
大家照旧怔了怔,紧接着发一阵呆。这种情绪无疑会传染人。“这又并不是哪个害他的。”下铺的第二个瘦斤斤帅气同学长吐口气说。“当内心已经觉得,或者说承认自己非离开不可,恐怕唯有下地狱一条路可走。”他们想重新唤醒被诅咒的爱,才发现已耗尽了所有的心血。当有某个日子,惊骇和诚意都换不来救赎的时候,出人意料,连做梦都不会再有色彩,这恐怕就是内心深处那个火山口命中注定了会突然喷发的时刻。那么,就痛恨自己吧!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