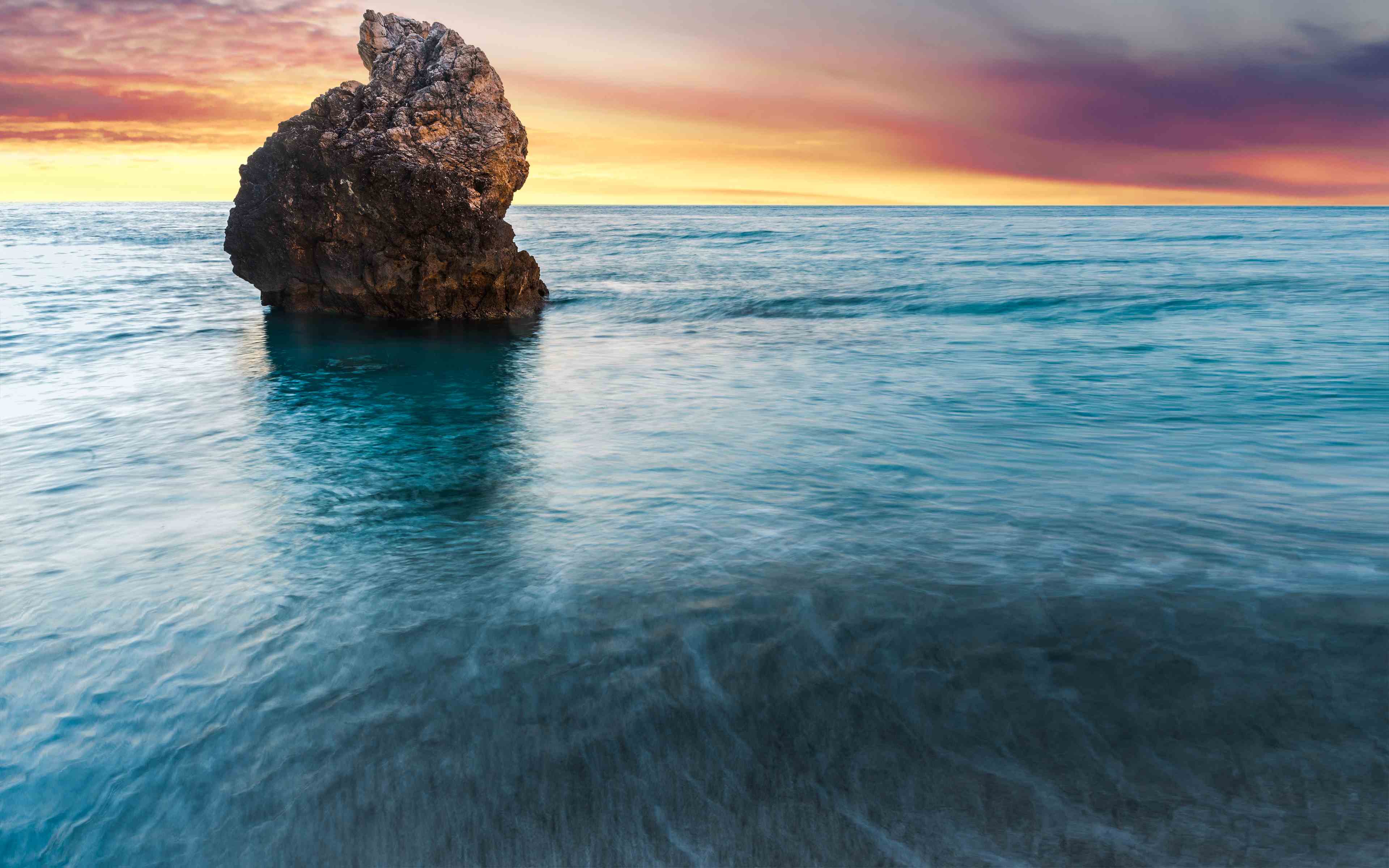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荒睡
日头劳作了一天,累了;一屁股坐在山巅,福着脸看山。
山虽是个冷峻的汉子,却也被绕在腰际的霞撩得直喘气。到后来,那气也就越喘越粗,终于喘出无限暮霭来。
月亮是个情种,荡着身子,款款迫赶日头。大约是傅粉调朱误了时辰,结果登上山顶,已寻不见日头的踪影。月亮也不气馁,软笑着,仍一步一景的走,矜持的很。
山顶自然青葱,松不多,有几棵;柏不多,有几棵。松柏性傲,争着抢着长在风口处,躯干虽不堪高,却有几搂粗细,伞状的冠,洒下半亩的荫。风来了,树冠细纹不动,风去了,枝柯摇曳起来,终于摇起一阵鸟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一个夜便醒了……有脚步声响起。
走近了,方看清是一个广额方颡的汉子。汉子肩一身行囊,抵近一棵松,贴着瞧。原来松的躯干上,刻着一打深深的圆。汉子揉揉眼睛,俯身再看,阔脸咔嚓一响,短了;抬手去摸,腮上嘭的一声绷出筋来。
汉子一歪肩,嗵的一声,抛下一身沉重,移过腿脚,稳稳坐了;抬手掏进怀里,捉出一只香烟,敬在鼻下,嗅一嗅,叼在嘴上,然后左兜右兜的掏摸,掏摸出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声轻响,手捧着点好,闷一口憋在胸腔,隐隐的痛了再把烟放出来,咧嘴一笑,随后有一口没一口的抽。一时间,满谷流淌的都是汉子的心事。
汉子抽罢烟,并不起身离去,双肘支在膝上,眯上眼晴,寻梦去了。
梦,自然斑斓;一个乡野女子,年华正好,虽是布衣服饰,却也不掩春色,尤其是肩头起花的绣工,散发着女子的居心一一这里的女子和男子一样砍山,百余斤的收获,担在肩上,崎岖路,水漂着走,不让须眉。衣肩处易损,损时便以山野之花为蓝本,锦绣覆盖,绣起之时,张家姐儿,李家妹儿,比一比,谁家姐儿、妹儿绣的神似,谁家姐儿、妹儿脸上就多几分妩媚,添几分怡情。
女子挽个包裹,匆匆走向村口,忽有相熟的言语传来,晓得是饭后扎堆谈今讲古的老者。心便悦悦慌,继而又慌悦悦的跳,迂至暗处,绞扭衣角,一下一下地绞,终于绞出一个决心;紧了紧鞋扣,拔腿奔向村后的山。
后山有一条小径,传说是彭雪枫将军遗失的“马鞭”,不信,却又不得不信;“马鞭”左兜又绕搭在山脊与村落之间,时而被沟壑掩着,时而又被峦峰托起。女子沿“马鞭”水漂着走,似是不忍用脚的重量,践踏它昔日的辉煌。终于攀上翠绿的顶,从兜里摸出一方手帕,贴着额沾一沾,然后把手帕当扇子用,扇着让粗气慢慢吐出;冲着一棵松,一羞涩,一软笑,一传递。
原来松下蹴着一个汉子。汉子也不客气,接过便打开看。轰隆一下,贲涨涨的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一一包裹里除了几双起底绣花的鞋垫,还盘着一双尺余长的头发辫子。汉子喉节一动,咽下一口唾沫,眼睛戳着女子的齐耳短发,直到眼里上了泪,才手抖着把包裹收入行囊,哑着嗓说:"俺走了,等月圆三十六次就回。每次月圆,你就在这棵松树上刻一个月婆,等你刻满三十六个月婆,那天夜黑,俺就在这里等你。"
女子剜了汉子一眼,饱满的羞涩,被汉子掏心扒肝的言语盘剥得窸窸窣窣,一层一层地脱落。那句久居胸腔的话突兀溜出了喉咙:"你回来,俺就过门儿!”
汉子呼吸急粗,一把捉过女子,满腔热血化作柔情,透过双手抚在女子的肩上,一下一下地揉搓,似是要揉搓掉那终日担山的艰辛。蓦地一把推开女子,嘣的一声,扯掉衫上那粒心窝处的扣子,交给女子,肩了行囊,转身而去。
女子倚了树干,眼睛虚望着支起耳朵;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终于远的像一个影子。女子先是鼻子一酸,又一酸,眼里就噙了泪,噙着噙着,那泪嘟噜一下,又嘟噜一下,就胖成了珠儿,胖成了珠儿的眼泪沿鼻翼潺潺滑落脚下,脚下金针铺地,一片柔软。
汉子眨眨眼,抬手从坐下拎出女子的发辫,托在鼻下,轻轻嗅,阔脸放出光来。
汉子对着发辫说:你咋刻了十二个月婆就不刻了?夜黑怕哩?怕个球哩,有月婆哩!说啥哩?全刻在心上了。嘿嘿,刻在心上好哩;风刮不走,雨打不掉,保险哩!说啥哩,想你不?嘿嘿,咋能不想哩?想的心窝子疼哩!记得野猪岭的小黑不?就是那个好唱歌的小黑。有天晚上几个工友喝高了,起哄架秧的请求小黑唱一曲解闷儿。小黑敝亮不持艺凌人,摆弄好拍抖音的设备,找个C位,抬头四十五度望着远方,同时兼顾眼前的观众,甩给大伙一曲,一时间,那诗一般的远方与活在当下的不容易反复揉搓起来。小黑歌唱的喧,他说唱歌简单,歌唱就难了,要有一种情绪在里边,音准可以修,情绪是修不了的。俺给你学两嗓子。
汉子抬手搓脸,四下望望,合了眼,发一个“滴哒滴哒滴哒"的音,夜便一下子静了下来,婆娑的树影似乎也退远了。汉子久不运嗓,粗粗嘎嘎,情韵风趣却在:
白发笑,
娃们那去了,
响麦炸豆一地粮,
看着心起焦。
大哥笑,
天涯海角漂,
一月挣上一年粮,
年根儿就回了。
大嫂笑,
月下磨镰刀,
年年双抢打头阵,
今年也跑不了。
乖男笑:
恋爱成本高,
无房无车无钞票,
工厂里死磕。
乖女笑,
行男那里找,
歪瓜裂枣不能要,
娘炮就拉倒。
……
月光一地青白,似是月亮烹饪时不小心弄撒的盐。汉子起手去摸,伸舌舔了舔手,果然是咸的,叹了。于是仰脸去看月亮。那月亮竟被汉子看得摇摇晃晃模糊起来。浸在歌子里的汉子,又絮叨起来:
工友们听小黑唱歌,先是笑,后来那笑声就像斧砍了一般,一下子断了。干工地的汉子和夜店女没啥两样,吃的都是青春饭,上了年纪就没人要了。伤了残了,甲方意思意思赔俩钱儿就给打法了。别以为干工地天黑了就可以下班,刮风下雨就不需要干活了;老板急着赶工期,工地人就得没时没点的加班。逢上有关部门检查,工地人更是得半夜三更去抢修,还会被莫名其妙的找茬,这儿扣点工资,那儿少发点奖金。传说中的工地三大美,下雨、停电、来美女。前两美基本享受不了,最后那个美是真美。尽管来的美女不是这个部门的监理,就是那个部门的经理,都是管人的人。可工友们还是喉咙干咽着,饿劳子见了肉包子似的能看直了眼。白天苦作倒没啥,到了夜里,工地上除了会喘气的男人,剩下的就是不会喘气的钢筋、水泥和砖头,这样的生活,心里干巴的要死。时间久了,就有人隔三差五的去夜店打桩。
一天,刚开工,工地上就来了一辆警车,下来几个便衣,把小黑铐走了。说是他把一个住别墅的小娘们给打桩了。后来才弄清楚,那个住别墅的小娘们是一个雇主家的小保姆。雇主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二人通过辛苦打拼,买了套海景房,为了还房贷,每天早出晚归。他们家的小保姆,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抱着他们家的孩子,在阳台上看海、喝咖啡、刷抖音。有一天,小保姆刷到了小黑,越看越稀罕,就不断的打赏,后来就约小黑到别墅里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小保姆对小黑说:有一次她洗澡时刷到了小黑更的新歌,那次就洗的特别干净,后来每次洗澡都听小黑的歌。小保姆边说边问小黑,你知道我为啥听你的歌就洗的特别干净吗?见小黑晃神的样子,就不在绕舌:因为你的歌声干净。小保姆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像得了花粉症一样泪莹莹的,缓过气的小黑看着大口喘气的小保姆,一下子扑了过去,抱起小保姆就在沙发揉搓;刚入巷,门就开了,雇主不响不夜的回来了。雇主一回来,小保姆的脸就不能看了,说小黑入室强暴她。小黑趁雇主不备窜了。唉,唱歌对小黑来说,就是给泛滥的痛苦找到了一个流淌的出口,心中的隐痛除了流淌在歌子里,还能在抖音上换些钱。多好的一手牌啊,他可好,上去就是王炸,最后剩下个三了;小黑的歌声是干净,小黑不干净了。
后来闷的扛不住了,俺就上街遛跶,有一次就遛到了图书馆,图书馆很大,人很多,有老有少,年轻人占了一大半,大家安静学习,这是一个学习的民族。在门口看了一阵子,忍不着就进去了。刚开始那会儿,眼一抹黑,不知道读啥书,想一想,还是读农林经管这方面的书吧,以后说不定还能用得上,终于不能自拔。知道了咱们那里的果子为啥那么好吃。原来咱们那里是冷凉气候帶。啥是冷凉气候带?就是地处六佰至三千米的山谷、河谷地带,这个位置昼夜温差大,果木养分易沉积。著书者说,谁先抢占了冷凉气候带,谁就是未来的胜者。俺就是这样眼睁着,耳开着,凡是实惠的章节,都先强印在脑子里。就这样读读抄抄,印在脑子里的东西,慢慢明白了。不明白的,要很久,突然有个机会,一下子就明白了。明白的越多,也就越容易明白。
日子久了,就和一个农林领域的老师成了书友,通过老师又认识了商界的一个书友。在城市里走走看看,看看走走,俺发现了城市人的那些颠倒事儿。啥颠倒事儿?嘿嘿,新鲜哩!他们把路边植树的地方用来盖楼,在家里栽盆景;去健身房拍照一小时,健身十分钟;回家睡觉穿睡衣,到影楼拍光屁股照;用排骨喂狗,吃咱们喂鸡的野菜;还说是绿色食品……
俺就是从这些颠倒事里看出了门道。咱们山上沟里坎里长的哪里是野菜野果,分明就是银条子金豆子哩。那个做商的书友说,咱们那里的野猪可是个宝哩,和优质的家猪杂交,繁衍的子一代猪作种,二代猪买到城市的大饭店,准抢手。书友说咱们哪儿是伏牛山的胳肢窝,是猪身上的里脊肉。就看你怎么弄,怎么吃了。还说咱们那里的地坑院也是个景哩。修整修整就是个大稀罕,城里人生活节奏快,需要减压的去处。书友建议俺回乡搞一个生态文旅合作社,有吃的住的玩的还有卖的。书友说,做农业简单,做好农业就不简单了,要想走得快,自已一个人走,要想走得远,大家一起走。书友说他愿意出一部分钱,算股金。俺把这事儿和咱的几个老乡说,他们也说这个事儿好着哩也想入股。俺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乡里县里跑跑,俺要办生态文旅合作社哩,请那些在外漂着的乡亲们回来自己给自己打工。啥?自己的庄稼自己种,心里踏实?你可真是隔着锅台上炕,没眼力劲儿;想干事儿不能看一时,看一时是雀蒙眼,雀蒙眼咋能长远哩……
汉子盯着"马鞭"瞧,嘿嘿的笑声透着云破月来般的豁亮。
"马鞭"上没有一个人影。
于是双从怀里捉出一支香烟,燃上那份期待,慢慢吃起。
月亮终于攀上山顶,又三下两下攀上树干,盘腿坐了,手却从枝隙间伸出,抢汉子手中的发辨。一下两下,总也抢不去。汉子眯着眼睛,嘿嘿笑。笑声漫开,撞了对面的壁,又颤颤地荡了回来。
"马鞭"上仍旧没有一个人影。
万籁俱寂,草间的虫子安逸的鼓噪着,一个夜越发的静了。
"马鞭"上仍旧没一个人影。
月亮也坐不住了,偏腿移下树干,向谷底滑去。汉子嚯地站起,瘸着腿移至峭壁边缘,一股入髓的寒意,自尾骨升起,沿脊柱上移,缠了颈,站了肩,压的双腿抖起来,低吟一声,如受伤的牯牛一般,滚下"马鞭“。
临近村口,腿脚就有些怯,石板路似一根母亲手中绵绵的线,把游子醉醉的牵着。没有灯光,狗一叫,灯亮了,狗成了灯的开关。
借着月光,汉子惊讶的发现,以自己家为终点,一路尽见残破的瓦砾,中间一座新起的楼格外显眼,走近了看,院门上,一把的寂寞锁头,陪着两个寂寞的门神。
汉子脖子一粗,眼框潮湿了。这是山根家。山根长汉子几岁,和汉子在一个城市不同的角落打工,一天,突起大风,山根一个趔趄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当时人就不中了。山根媳妇狠着心把山根烧了,抱个盒子回家埋了,然后用山根拿命换来的钱,为山根的父母起了楼。楼起那天,山根媳妇跪了:向山根父母磕了头,然后带上孩子一头扎进城里,挣命去了。
汉子整整衣衫,调理好情绪,喜着脸进了家。当着娘的面儿打开行囊,拿出给娘买的衣服,围绕着比一比,遮遮掩掩询问女子的消息。
当娘的心里一咯噔,放下虚举着的手,接过衣服,别过脸去拂新衣上的折子,犹犹豫豫断断续续告诉汉子:两年前岭上来了一个懂医术的后生,后生医好了女子病秧子的爹,女子没啥报达人家,就跟人家下山了。
汉子静静听了,腮上的咬筋一动,又一动,抬手掏进胸口,挖出一包烟,嗑出一支,张口叼了,打着火,挤了眼点好,三两口吃尽,嘴角一动,烟屁股飞向门外,抬手搓一搓脸,搓出一句娘听不懂的话:“没摔到峪里就好!"再看那张阔脸,已平静得如一盆不见风的水了。晃至耳房,息下。
次日,天将午,落了雨。初时如一个斯文的书生,磨磨唧唧地下,后来就像一个发了脾气的汉子,扯天蔓地下了起来。一个时晨左右,徒然收了。雨后的天空,滋生出一种力量,生生把人往户外拽。
长接短送。落雨时,汉子的娘和了面,用一块湿布盖了,省着。中间又揉了几回,扳倒的媳妇揉倒的面,这样擀出的面才筋道,有嚼头。雨住时,面已潇潇洒洒地切好,天长地久,一案的奢侈。
忽然的,就想起汉子儿时塞面时的枝枝蔓蔓一一中原一隅,管吃叫怼。如锅滚豆烂,下一把鸡毛菜,加盐后掩了面糊,溜底搅上几回,不稀不稠的一锅,熟了。做娘的当院扯上一嗓:“汤中了,怼吧!"于是一干儿女,狼一样卷进灶火,乒乒乓乓地盛饭,屋椽下,长筷大碗,或蹲或倚,喜着脸,勾着头,欢欢腾腾地怼。先是沿碗边薄薄地吸溜一口,转一下,又沿碗边薄薄地吸溜一口,如是者三五回,之后便小口变大口地呼噜。老货们不急,搅着喝,偶尔吃到一粒豆,镇定地慢慢嚼,少崽们并不搅,把稠的沉淀在碗底,最后扒拉进嘴里,扬着脸嚼,真过隐。老货看见温温的笑,对先喝完的崽子大声说:再怼一碗?因为食物的单调,那吞咽声一波一波起落有致,有如民乐一般,一个世界被震得晃荡起来。于是由此"怼"联想到东北那疙瘩的“塞”,推敲起来,一样的生猛、远古,亲切的让你放下矜持。
净锅,添水,点火。隙间捣了蒜汁,放了麻油,搅一搅,兑醋、兑水,再搅一搅,蒜捣里飘起一层圆润的油花,闻一闻,一张脸就福得不行一一大约一个人遇到高兴的事儿,都是这个样子吧。
水沸时,扯嗓唤着汉子的小名起床怼面。没个应声。寻到耳房,亦不见个人影。偌大的板床上,盘着一双女人的发辨。
许久,汉子的娘才缓过神,着火一般扯开院门,咣当一声,一团脚印轰然作响砸在面前。脚印在院门外盘桓又盘桓,最终迤逦踏向通向村口的“马鞭"。
汉子娘哑言。蹴身抚摸汉子的脚印。忽然觉得手上有些微的异样,原来不知何时,土狗大黄,孝儿一般蹲在面前,卷着舌,一下一下地舔汉子娘的面手。
大黄觉得主人的手有些颤,脸色也不及往日清朗,于是便凄着眼摇着尾,嘴里呜呜咽咽起来,似是安慰,又似是担忧。
汉子娘不能再忍,一把揽过大黄,如揽了亲儿一般,抖着身,压着喉哭,一嘟噜一嘟噜的眼泪,豆子一般,种在汉子的脚印里。忽然的又一把推开大黄,板了腰,像是对大黄,又像是对自己说:“咋的啦?还哭上了?狼行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俺儿是狼哩,走千里吃千里,哭的那门子?丢你的先人哩!"
汉子娘调理过滞气,整个人又豁亮起来。峥嵘的脸上泛起的不再是惜别的柔软,而是一层坚硬的欣慰。噼噼啪啪拍着面手,转身寻来一只木盆,咣通一声,扣着一个脚印,脸上的坚硬又深了一层。
大黄跟在主人的身后,欢欢腾腾地摇着尾,迭次吠起,仿佛借机发泄心中的不痛快一一狗走千里,一定是吃屎吗?
日子被节令撵着,踉跄地跑,小满一过,布谷鸟就来了,日复一日地在天空盘桓,重复着祖传的那句短歌:"割麦,垛垛!割麦,垛垛!"一个世界慌慌的、喜喜的,农事来了。
自打分地单干后,乡亲们一年就夸越了“温保线",却几十年进不了“富裕门”,粮食不主贵了;于是青壮的一群,舍家撇业纷纷扎进都市的旮旮旯旯找钱去了。留守的老人叹了:备下吃的烧的就能活!干啥非要把日子过个稀碎?这些在土地上刨希望的一辈人,视土地如命,认准一个理:秋分种下一袋麦子,夏季收获二十袋,收成除了自家吃还能换钱,一袋变二十袋还嫌少,心里的秤杆偏了。叹罢拧动着老腰挪到田头地脑热血澎湃的苦作,间隙锤膝拍腰,说些老了没有用了的话。从此,风里、雨里,白雪覆盖的岭头,只剩下几根拐枝们撑着,还有几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嫂子们,当然还有几行深深浅浅的狗瓜子印,从村庄的一头延伸到村庄的另一头。一个留守的嫂子感叹了;悄不声的找了几个同样留守的嫂子,商量着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帮衬着山岰里老幼的日月。无非是农闲时,看看谁家的柴垛矮了给砍捆柴,谁家的水缸浅了给担担水,都是手拿巴掐的活儿,不算个啥。农事来的时候,紧忙自己的,忙完自己的,咬咬呀,踉跄着再去忙东邻西邻的。事主感激着,递茶、留饭,茶喝了,饭却不吃。嫂子们说,谁家没个春夏秋冬。说罢慢慢走回家,赶猪,唤狗,圈鸡,关院门,打了水,一屁股坐在檐下,畅出气,慢慢洗。想一想明响儿的活路,忽然起身踉跄着奔向灶火,叮叮当当准备明响地头的干粮。夏收全没秋收的散逸,崔命哩!
一日,嫂子们担山回,在“马鞭"撞见一个白衣女子。白衣女子腰里似别着什么高兴的事儿,一跳一跳的走,仿佛是草间跳动的一只白羊。嫂子们正隔皮见瓤地打量着白衣女子,白衣女子便直脖子正脸的到了跟前,黑瓷瓷的眼仁似泡在油中的辣子,灼得嫂子们不能久看,胸前的两陀肉,晃得嫂子们红了脸。于是慌忙压着心跳,闪在一旁。白衣女子道一声谢,猿步登向后山。
嫂子们一脸疑惑,眼睛轱辘来轱辘去,方才觉出那声"谢谢"不是本地口音。
怔忡之际,头顶传来一阵翅膀扇动的声音;鸟雀们在这一刻归巢了。嫂子们回眸一望,只见日头赤着面软着身坐在山巅,左涂涂,右画画,一副不愿离去的样子。一片红雾,在涂涂画画中洇开。一个嫂子指着日头说:“也是个劳碌命!”其它嫂子齐看齐笑。笑声还未落地,那日头已不见了踪影。嫂子们一惊,继而齐声笑了起来;大约,一定是息下了吧。
天依然亮。"马鞭"却暗了下来。嫂子们望着白衣女子消失的方向,担了一颗心,于是卸下一身沉重,尾随而去。
月亮隐在东山的崖隙间,崖顶便黄黄的亮,一挣,露出了半边脸,嫂子们暗暗使了一把劲儿,又一挣,果然就露出了整个面孔;嫂子们松了口气,“马鞭”一下子亮了许多。
白衣女子攀上山顶,来到一颗松下,绕着树走,择一光亮处站了,仰脸和月亮比灿。大约过了七八个周天,才收住心神,打开肩包,摸出一把利刃。嫂子们一惊,正要施救,那利刃却抹向松树的躯干。一下一下地用力,终于歇手,又移着身子看了一回,收了刀具;却又侧脸贴了松,结结实实的抱了。抱着抱着,就抱出了一抖擞一抖擞的哽咽。嫂子们正疑日怪了,白衣女子竟娇娇巧巧景景致致唱了起来:
梳洗呀,
打扮呐,
着工装啊,
载上家什卖扁食,
开到工地旁呐啊。
哎嗨哟,
开到工地旁呐啊。
大喊呐三声呀,
卖扁食啊,
惊动了饭点下班的人呀,
都来吃扁食啊。
哎嗨哟,
都来吃扁食啊。
卖扁食喽!
……
声随情起,情于腔融。那首嫂子们做姑娘时常哼的民歌,被白衣女子改编的又地道又温婉;一下子唱到了嫂子们的心坎上。一个嫂子也情不自禁的景致起来:"大妹子,扁食啥馅儿呀?”
白衣女子一惊,张开的嘴巴一下子僵着了。举目四顾,并不见一个人影。于是手捂肩包,逃也似的奔向"马鞭"。
一个嫂子一叠声的埋怨那个多舌的嫂子,其它嫂子复和着。正愦憾呢,"马鞭“上忽然又有歌声荡起:
葱花啊,
姜丝啊,
鸡蛋丝啊。
内有作料肉疙丁,
吃着香喷喷啊。
哎嗨哟,
吃着香喷喷啊。
……
歌声透着古松般的清韵。
嫂子们虽然过了耳隐,可还是觉得日怪。于是鱼惯涌到松下,只见一棵松的躯干上,刻着两行深深的圆。首行十二个,次行一个。那个新刻的圆,正在汩汩流泪。
山里嫂子,自然熟谙本土风情。只是道不明白,白衣女子情系何人。于是便掰着指头猜。其间插科打诨,话野的叫草木乱颤。正闹着,一个嫂子蓦地喊出汉子的名讳;说,那圆多象他发怒时的眼。大伙齐看,齐说,象!便贴近了瞧,惊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嫂子们从那些圆里,看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哪里呈现的仿佛是汉子述说的生态文旅合作社,嫂子们的死鬼男人们,正在那些建筑物里骑锅夹灶的忙活着。所有的窗眼,都死盯着圆里的人眼。
一时间,一个世界静得空虚起来。嫂子们的身影,被月亮挨个书写成了惊叹号。那惊叹号如棍子一般,挍动着那突兀袭来的串串相思,把个泼泼辣辣的嫂子,瞬间挍成温温柔柔的小女人了。
嫂子们想自己的死鬼男人了。嫂子们做姑娘时也想过男人,那些想是不着边际的素净想,结了婚经过男人拾掇过的身子,再断了男人的拾掇,那想就成了中心思想的想了,中心思想的想磨人哩。
一个嫂子“啊”了一声,手抚胸口蹲了下去。之后东摸摸西碰碰,摸摸碰碰中,恍惚觉得自己的死鬼男人在缠自己的颈,压自己的腿。情急之下就伸手抱了那个死鬼,后来就眯了眼,任那死鬼把自己压了,一种久违的潮湿,牵枝蔓叶地袭击了嫂子的身休。忽然感到了异样,那死鬼的身子咋是凉的哩?睁眼一看,自己怀里抱的竟是一方山石。轰隆一下,心里就塌了一个坑,泪就下来了,温暖的嫂子,一下子无措了,瘫坐在那里一口一口地喘气儿。
一个毛脚嫂子不知啥缘由,话急了就走了调:"咦,你这是弄啥嘞?弄啥嘞?"
一个精细的嫂子抬手指了指盘坐在树梢上的月亮,又捅了一下毛脚嫂子紧绷绷的屁股。毛脚嫂子一扬脸,先是木了一下,接着眸中生出一种脆生生的光,想起把自己交出去的那个夜晚,不也是在大月亮地么?一瞬间,一颗平平展展的心,一下子波波澜澜了;腿一软,跌出一句骂:"该死的月婆,又磨人哩!"
一个嫂子“吞儿"笑了,众嫂子“吞儿“的一声加入进来,一个夜一下子芬芳起来。
哭过了,笑过了,嫂子们跺跺脚,又跺跺脚,掮了弃下的收获,哑言走下“马鞭"。
圈鸡,唤狗,栏里看看,作完一日的夜课,这才温了水洗了。想一想,寻出一面镜子,照照;一身精白的肉,脖子、脸、手却是黑红黑红的,化了妆一般。于是又翻箱倒柜的找,终于寻到一瓶脸霜,并不看保质期,慢慢抹擦,渐渐的兴奋起来,舔一舔嘴,有曲自喉中流出:
田不孬
地没荒
爹娘扎实娃健康
院门拴
屋里寒
寂寞垒起屋后山
白天想
黑夜念
一年布你八九晚
哎呦呦
哎呦呦
你咋死的那么远
……
腮上有泪,痒痒的,发觉了急慌慌擦去,四下里看看,竟有些惭愧。夜半,荒睡的大板床上,平添了一种梦话。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