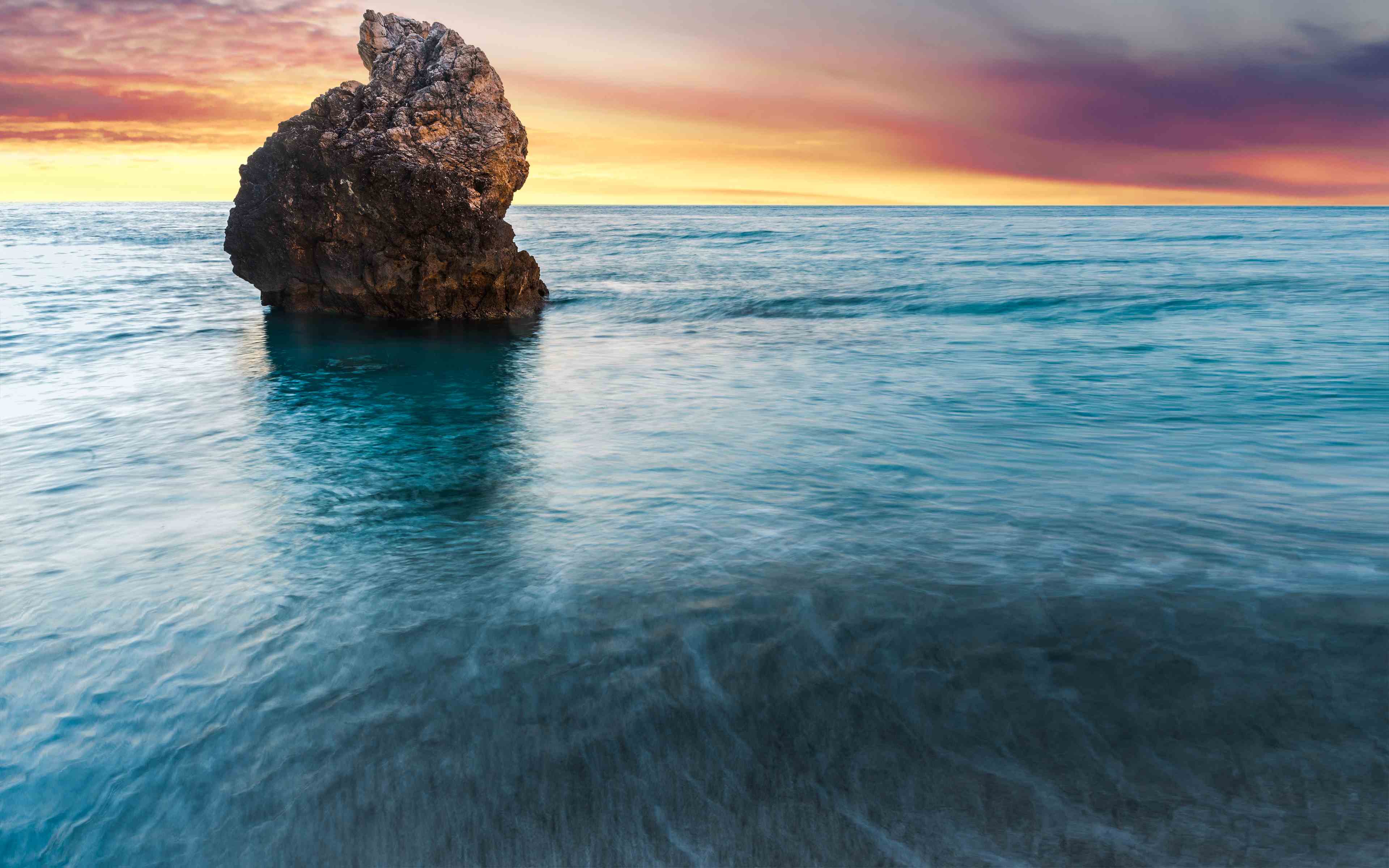中华228和229哪个好(读了鲁迅的文艺理论批评,你就知道如何评价“屎尿体”诗歌了)
鲁迅先生
鲁迅是栖于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两大领域的伟大作家和批评家。他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至今仍然具有经典性,有着重要的现实启悟。
一、公正——“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坚持公正的立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正是鲁迅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第一条原则。
左联盟友茅盾的《子夜》出版以后,1933年5月15日《新垒》杂志第1卷第5期发表署名焰生的《〈子夜〉在社会史的价值》一文,说:“《子夜》的文艺价值虽不能超于社会史的价值,但可以说是文坛仅见的杰作,而以阿Q传而沾沾自喜,躲在翻译案头而斤斤于文坛地位保持的鲁迅,不免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至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1卷第79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0月版[下同]。)借《子夜》的问世讽刺鲁迅。其实,不过是无知妄说,作品的价值是不以篇幅的大小、字数的多少为标准的。《子夜》不愧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杰作,但无论如何其思想意义是不能与《阿Q正传》相比的。以《子夜》贬低鲁迅,只是出于对鲁迅的恶意罢了,但鲁迅却不仅没有丝毫介意,而且对《子夜》的出版欣喜之极,在1933年2月9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喜悦地告知:“我们这面,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然而他也并没有把《子夜》看得十全十美,当木刻家吴渤来信说起《子夜》的不足时,鲁迅又在1933年12月13日的回信中说:“《子夜》诚如来信所说,但现在也无更好的长篇作品这只是作用于智识阶级的作品而已。能够更永久的东西,我也举不出。”
我们如今重温鲁迅的对待《子夜》的态度,不能不由衷地钦佩他的公正:既为盟友的作品而喜悦,丝毫没有常人的嫉妒之心,又没有“举之上天”,而是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文艺作品的好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在没有更好的东西时,我们只能肯定那些相对比较好的作品。《子夜》也确如鲁迅所言“只是作用于智识阶级的作品”,对工人群众的描写并不成功。鲁迅的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众所周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之后,关系一直不好,对周作人的许多作为,鲁迅都持批判态度。但这并没有使他失去对周作人散文价值的赞誉,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把周作人看成中国优秀散文家的第一人 (见《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当时属于京派的沈从文,鲁迅从政治上也持批判态度,《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所批的炯之就是沈从文,但也并没有因此否定他的小说艺术,在同一谈话中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
鲁迅对评述的对象“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始终“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保持着一位内行批评家的公正态度。
而对那些反动的东西和抄袭的现象,鲁迅是绝不留情的。上世纪30年代初泛起一股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逆流,鲁迅一反多写短文的常规,写了长篇论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予以犀利的批判。并在《刀“式”辩》一文中,尖锐揭露他们的“大作”《鸭绿江畔》抄袭法捷耶夫《毁灭》的行为:“《毁灭》的译本,开头是——‘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真如郁达夫所言:“鲁迅的文体简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 (郁达夫:《〈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8月版。)“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两地书·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页)。
文艺理论批评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文艺作品的价值不因“不虞之誉”而增加,亦不因“求全之毁”而减少。只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对文艺作品进行恰如其分的评论,才能探寻到文学的底蕴和内在的规律,促进文艺的发展。当然,要真正做到这点,绝非易事,不仅要对文学艺术真正内行,而且需要有作为评论家的道德,那种“举之上天”、人为拔高的捧场性的“有偿评论”、“人情评论”,或者“按之入地”的否定一切的嫉妒性“酷评”,都是违背鲁迅所倡导的文艺理论批评原则,有害于文艺发展的。鲁迅是最反对“商贾的批评” (《商贾的批评》,《鲁迅全集》第5卷第591页。)的。
二、真实——文学艺术最基本的准则
真实是鲁迅文艺理论批评最基本的准则。鲁迅的价值也就正在于以振聋发聩的呐喊,促使中华民族从“瞒和骗”的大泽中猛醒,“睁了眼看”现实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鲁迅无论是在对同代文学作品的批评,还是在文学史研究中,都始终坚持真实的原则。
他1933年5月25日在给周茨石的信中说:“(1)如办刊物,最好不要弄成文学杂志,而只给读者以一种诚实的材料;(2)用这些材料做小说自然也可以的,但不要夸张及腹测,而只将所见所闻的老老实实的写出来就好。” (《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9页。)1935年2月4日夜在给木刻家李桦的信中说:“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漩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 (《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2页。)真实,始终是鲁迅评价文艺作品的第一要旨:“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 (《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鲁迅全集》第6卷第241、242页。)“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 ,因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 (《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6卷第340、341页。)对于现代小说,他赞许鸿敬熙“只求描写的忠实”的创作态度,不赞成杨振声“忠实于主观”、“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的做法,认为他按照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玉君》“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248页)。在文学史研究中,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红楼梦》讲出了千古名言:“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8页。)
总之,在鲁迅那里,真实是文学艺术最基本的准则。
三、深刻——显示出“人的灵魂的深”
鲁迅在《〈穷人〉小引》中引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名言:“人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 (《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105页。)
鲁迅很欣赏这句话,称陀氏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的《祝福》把祥林嫂一步步置于灵魂的拷问,死之前还发出最后的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彷徨·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7页。)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也是对人类灵魂的审问。他在创作中这样做,在批评中也以“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为最高标准。
鲁迅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俄国作家阿尔支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翻译呢?就在于它反映人的灵魂有一定的深度,阿尔支跋绥夫的“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译文序跋集·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第10卷第183页)。鲁迅在《记谈话》中说道:“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什么相像呢?就是灵魂相像。鲁迅说:“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由此想到“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张献忠“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375-377页。)由绥惠略夫的灵魂而想到张献忠及中国人的灵魂,以及几十年以后许多改革者的境遇与灵魂,这就是鲁迅在批评和解读作品时的深刻性。
鲁迅还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另一作品《幸福》。这篇小说写妓女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的娱乐,及至烂了鼻子,只能而且还要以肉体供人残酷的娱乐。一个过客让她脱光衣服,站在雪地上,由他用手杖打十下,就给她五个金卢布。赛式加为了生活,只好照办,被打得鲜血直流,痛苦不堪。但是当她拿到五个金卢布之后,就“迈开发抖的腿向市上走去,金圆在捏紧的手中。衣服擦着伊的身体,给伊非常的痛楚。但伊并不理会这件事。伊的全存在已经充满了幸福的感情……吃,暖,安心和烧酒。不一刻,伊早忘却,伊方才被人毒打了。” ([俄国]M·阿尔志跋绥夫著,鲁迅译《幸福》,《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鲁迅指出:不仅赛式加并非幸福者,“而且路人也并非幸福者,别有将他作为娱乐的资料的人。凡有太饱的以及饿过的人们,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为生存而取过这类的娱乐与娱乐过路人,只要脑子清楚的,一定会觉得战栗!” (《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188页。)
的确是深刻得令人战栗!鲁迅看到了其中的深刻,也解读出了这令人战栗的深刻!
鲁迅文艺理论批评的深刻性,还表现在对《狭的笼》的评论中。《狭的笼》是俄国盲诗人埃罗先珂创作集《天明前之歌》里的第一篇,是作者在漂流印度时有感于当地人对废除“撒提”习俗的不满而写成的。鲁迅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在附记中这样评述道:“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所谓“撒提”,是印度旧时的一种封建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即随同丈夫的尸体自焚。“撒提”(Sait,梵文)原义为“贞节的妇女”。对于这种极端残忍、灭绝人性的封建习俗,予以废除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的许多印度人,甚至包括很多上层的文化人都表示反对。这些人的确如鲁迅所说的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争取“人”的价格,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因而“即使并无敌人”,没有殖民者、奴隶主形式上的统治,在精神上、内心里,他们仍然是“狭的笼”中的最可悲的奴隶!鲁迅揭示出这篇作品中所显示的“人的灵魂的深”!
上世纪80年代初,廖冰兄画了一幅很有名的漫画,题为《自嘲》。画的是一个蜷缩成一团的知识分子,看来原来是被囚于罐中的,如今罐虽已被打碎,他却仍然保持着囚禁在罐中的姿态。1994年冬天我去参观黄胄办的炎黄艺术馆时,见到这幅画作为藏品陈列,令我长久伫立画前,想得很多很多。今年3月,中国美术馆又举办了《冰魂雪魄——廖冰兄漫画展》,更把这幅《自嘲》放在中心位置。那位罐碎后仍然蜷缩一团的知识分子,以至于“狭的笼”中的“下流的奴隶”,实质上属于同一个精神体系——由奴隶的思维模式、心理模具压锻、腌制出的“奴在心者”型号。这种型号的“精神奴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的。我们有必要时时反思自己是否有这样的精神状况,深刻反省自己的灵魂。
四、审美——老熟、细腻的艺术感觉
鲁迅在文艺研究批评中,是很重视审美的。他具有天赋的老熟而细腻的艺术感觉。
我们先举一个小例子,鲁迅在《“大雪纷飞”》一文中说:“《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花边文学·“大雪纷飞”》,《鲁迅全集》第5卷第582页。)
从“那雪正下得紧”中的“紧”字,感到了“好得远”的“神韵”!该是多么老熟而细腻的艺术感觉啊!这正是一种绝少有人产生的细微“语感”,如汪曾祺所说能够“扪触”到语言 (汪曾祺:《“揉面”——谈语言》,《晚翠文谈新编》第107页,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体悟出其中的“神韵”。
有人看到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过:“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鲁迅全集》第4卷第373-374页。)就认为鲁迅是否定中国传统文论的,其实是一种误读。鲁迅说这话与在《青年必读书》中所说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一样,是有特定环境与特定对象的。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确实引进外国先进的文艺理论书籍,乃当务之急。为了突出强调这一点,鲁迅提出了“多看外国书”的观点。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后来他在《答“兼示”》一文特地做过解释,说误读者是“忽略了时候和环境” (《准风月谈·答“兼示”》,《鲁迅全集》第5卷第377页。)。
从神髓上体味,鲁迅的文艺理论批评深得中国古典文论的审美要旨,这从他的文学史研究著作中可以深切体会到。
一个文艺理论批评家或文学史家,审美能力的高低,艺术感觉的细粗,衡量的标准就在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能否做出精炼恰切的评骘,分清不同的档次,对其不同特点予以准确的概括,并能探究其中的原因。这一点,在鲁迅对《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评述中,格外分明地表现出来了。
清末民初,李宝嘉托名“南亭亭长”而作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假名“我佛山人”而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很盛行。鲁迅却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这两部书同样是“描写社会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比起《儒林外史》,“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及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5页。)所以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惟将《儒林外史》列为“讽刺小说”,专篇论述,认为其“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之所描写者,“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28、229、231页。)《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只能列为谴责小说,因其“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中国古典文论特别强调“婉曲”与“含蓄”。从鲁迅对《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比较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出鲁迅是深得古典文论要旨,深悟其“神韵”的。
鲁迅在评论文艺作品时,非常注意细节描写。因为文学实质上是细节的艺术呈现。鲁迅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擅长细节描写,在评骘别人的作品时对细节也极为敏感。例如《中国小说史略》评述《儒林外史》时特引了范进丧母后,酒席宴上,知县以为他居丧尽礼,不用荤酒,但“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同上,第232页。)对这一细节,鲁迅评论道:《儒林外史》“刻画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都亦屡见”。善于发现文艺作品中的精湛细节,道出其中妙处,应该是文艺评论最见功力之处。在这一点上,鲁迅可说是无人比肩的,很值得当今文艺评论家们悉心体悟。
凭着这种高超的审美能力和渊博的学识造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那些真有文采的文学家作出了扼要评述和精辟的概括,如对屈原《离骚》的概括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对司马迁《史记》的概括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第382、435页。),皆流传千古。
从鲁迅对中国古典绘画的评骘,也可以看出他的审美能力之强,艺术感觉之细。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有这样一段精妙的论述:“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第24页。)如不是真正把文学和书画等等古今中外的各种艺术门类弄得通透了,“透入”文学艺术的内在韵律,怎么可能写出这般绝妙的文字?
陈独秀于1937年11月21日在上海《宇宙风》10日刊52期上刊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汇编》第2卷第884页。)一文,称“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这里所指的天才当然首先是文学天才。人类,特别是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是存在天才的。在文学上,是有一些人具有超常丰富的想象力与感应力,尤其对语言文字具有非常突出的敏锐而细腻的天赋感觉。他们不仅自己善于运用语言文字,而且对别人的语言文字也极为敏感,能够灵敏地发现语言文字的美,与写出美的文字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认为,在上世纪左翼作家群中,有一男一女,最有文学天才,对语言文字有一种天赋的灵感。男的是柔石,女的是萧红。而这两个人都是鲁迅所发现的,鲁迅对他们有一种发自心灵的欣赏和亲切感。有人甚至说鲁迅与萧红是精神恋爱,恐怕未必确当,但在文学艺术的审美感觉上相通相知,却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种天赋的审美能力,一种对语言文字的天赋的美感。
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一定要具有这种审美能力。
五、历史——在历史发展中进行评说
鲁迅的文学理论批评原则,一是公正,二是真实,三是深刻,四是审美,但他又不是从单一的方面进行评论,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以对历史的前进是否有益为综合目标,衡定文学艺术作品的高低优劣的。
《白莽作〈孩儿塔〉序》就分明地表现了鲁迅的这一立场:“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纵然鲁迅对文艺作品有很强的审美要求,但是他的根本原则,不是看其是否“圆熟简练,静穆幽远”,而是看其是否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否站在新生事物一边。他是把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放在首位的。
当有人攻击杂文时,鲁迅回应道:“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鲁迅的写作从始至终都是为了“救中国!”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伟大复兴,这是他评判文艺作品的价值的基点。他从来没有以纯文学或纯美文的角度评论过任何文艺作品,这在鲁迅一生中是一而贯之的。
上世纪30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争也充分表现出鲁迅的这一立场。他在《杂谈小品文》强调文章应“有骨力”。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又说:“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镳。”“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如此评论小品文等文艺作品,正在于他“没有忘记天下”,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水深火热之中!他与林语堂关于幽默之争,其实并不是反对幽默本身,鲁迅本人就是20世纪中国真正的幽默大师,而是因为当时的形势下容不得置苦难的人民于不顾,自己躲到象牙之塔中玩什么“幽默”!
六、文体——鲁迅式的批评文体
鲁迅的文艺理论批评有他独特的风格,形成了一种鲁迅式的批评文体。
这种文体从来没有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地摆架子、耍洋词,而是以中国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态度和语言娓娓而谈,切中肯綮。每篇都是地道的美文,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段,作出精辟的概括。
就拿我们前文所说过的鲁迅评论柔石和萧红的两篇文章来说吧,《柔石作〈二月〉小引》非常深刻、中肯地评论了主人公萧涧秋的性格:“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尖锐地指出了萧涧秋的弱点,但并没有否定他,肯定“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53、154页。)。这样的人物评判是全面、透辟的,也是很少有的。而对柔石《二月》的艺术风格,则用“工妙”二字概括,实在精辟之极,比有些长篇大论准确、传神得多!鲁迅的这篇评论其实同是一篇“工妙”的美文。《萧红作〈生死场〉序》,闲散地从1931年日本入侵上海的“一·二八”事件谈起,说到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的情景,看似无关闲笔,其实正与《生死场》所描写的东北遭日本侵占的惨景相对照,令人“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简劲地概括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至于艺术性,则更为“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422页。)。虽然仅千把字,却写得散淡、老成,切中肯綮。像这样的文学评论文章,如今是极少见的。
总之,这种鲁迅式的批评文体,在现今很值得珍惜和研究。
结 语
总括来说,鲁迅的文艺理论批评对现实具有如下启悟:
一、坚持公正的立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反对“商贾的批评”,也拒绝否定一切的“酷评”。
二、坚持真实这一文学艺术最基本的准则,对敢于讲真话的作品要大胆支持,对那种“瞒和骗”的所谓“文学”要敢于揭露。
三、坚持深刻的高标准,对于那些显示出“人的灵魂的深”的作品,要善于发现,勇于表彰。
四、注意审美,力求保持细腻的艺术感觉,能够品味出作品境界的高低优劣,探索艺术的美的规律。
五、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历史发展中进行综合评说,把社会效应放在首位。
六、须磨砺文体,学习鲁迅式的批评文体,不要摆架子、耍洋词地空论,而要努力将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写成美文。
鲁迅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与他的创作一样光照日月,千古不朽,对现实有着无尽的启悟。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