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有幸
福星高照
薛邃老教师的画,通古、古代、属于将来,我们今天能与“邃”遇,真是福星高照。
谐音梗大行其道的今天,也玩到了薛邃老教师这厢。晚辈为白叟办画展,起的名字,不是“‘邃’心所欲”,就是“‘邃’遇而安”。这种小机敏小把戏,白叟不见得喜好,却眉开眼笑,说“蛮好蛮好”。
若摘掉眼镜,留起长髯,眉开眼笑的薛老,就是人见人爱的老寿星,完全不必扮装。
薛白叟好,人见人爱,却不容易见到。由于他不喜好出头出面。偶尔为提携晚辈,列席画展,也留下用饭,他笑眯眯坐着,不发一言。但是,暗里里,薛总是很健谈的。
薛老画好,人见人爱,也不容易见到。由于他不喜好宣传炒作。他一门心思,就在家里画画。假如硬要说薛老有什么喜好,那就是访山问水,师法天然。可惜,三年疫情,白叟未再进山。提及不克不及出行的遗憾,薛老却只怪本人腿脚不复昔日之健。
艺术家,常有些风雅做派,以示不凡。薛老却不,他跟寻常老头别无二致。字画家高寿,也有些特别习气,好比刻印曰“八十后作”,好比落款曰“年方九十”。薛老却不,他年登鲐背,常常只落一个“邃”,乃至只盖印不落款。他,不休在做减法。
薛老真是一位隐者呢,比年事也隐了。所谓“大隐隐于市”,形诸薛老,固然是确切的。但,这并不是薛老的寻求。他,只是一门心思画画。
我熟悉薛老时,他八十了。我万万没推测,将来的日子里,带来惊喜最多的画家,居然是他。与薛老徐徐熟了,我才晓得,就在年登耄耋时分,薛老买通了中国画的一切经脉,步入自在王国。他不再只是一位笔墨干练、法度威严的传统山川画家。他的画,以前无法将其归类。他自在游走于山川、人物、花鸟画之间,胜似闲庭信步,洒脱安闲。他画中的人、鸟、兽、树、花、草、石、亭,那么古意盎然,又那么新意迭出;他笔下的各式样貌,你先是惊叹向来没有见过,又会以为妥帖极了,就应该谁人样子。每一次见薛老,他的画总能让我们惊喜地叫作声来,他向来不会反复从前,不管是他人,照旧本人。几乎每一幅,都在出新,几乎每一笔,都有妙思。薛老的妙思啊,如山间的响泉,汩汩而出,欢然奔涌。我们作为薛老的观者,也似山间的访客,掬一捧山泉,享其甘美,赞其清冽,观其向前。
薛老的画,通古。“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用这句诗,说薛老的画,是贴切的,但又是浅薄的。薛老画里的灵气与古意,不在形,而在神。他饱读诗书,善填词赋诗,有一次,薛老用昆山话诵读了他写的一组题画小令,我和一同倾听的顾村言兄直呼如遇前人。比年,他画了很多诗意册,陶渊明、孟浩然、苏东坡、范成大、姜白石……他是真的与前人意通神合,才干画出那些诗境。他就是一位活在当下的古之逸人。
薛老的画,古代。他曾考进浙美油画系,后因病辍学。他对东方美术史烂熟于胸,他晓得毕加索、马蒂斯的线条从何而来。他见前人所未见,以是,他能画出笼统离骚、意态山川,道前人未道,启今世人幽思。
薛老的画,属于将来。他的诗情、他的哲思、他的伶俐、他的悲悯,经过笔墨,留在纸上,直抵民意,也必将传诸后代。对中国美术史有博识研讨的龚继先教师说:“薛老的画,要进博物馆的。”
薛老的画,通古、古代、属于将来,我们今天能与“邃”遇,真是福星高照。(江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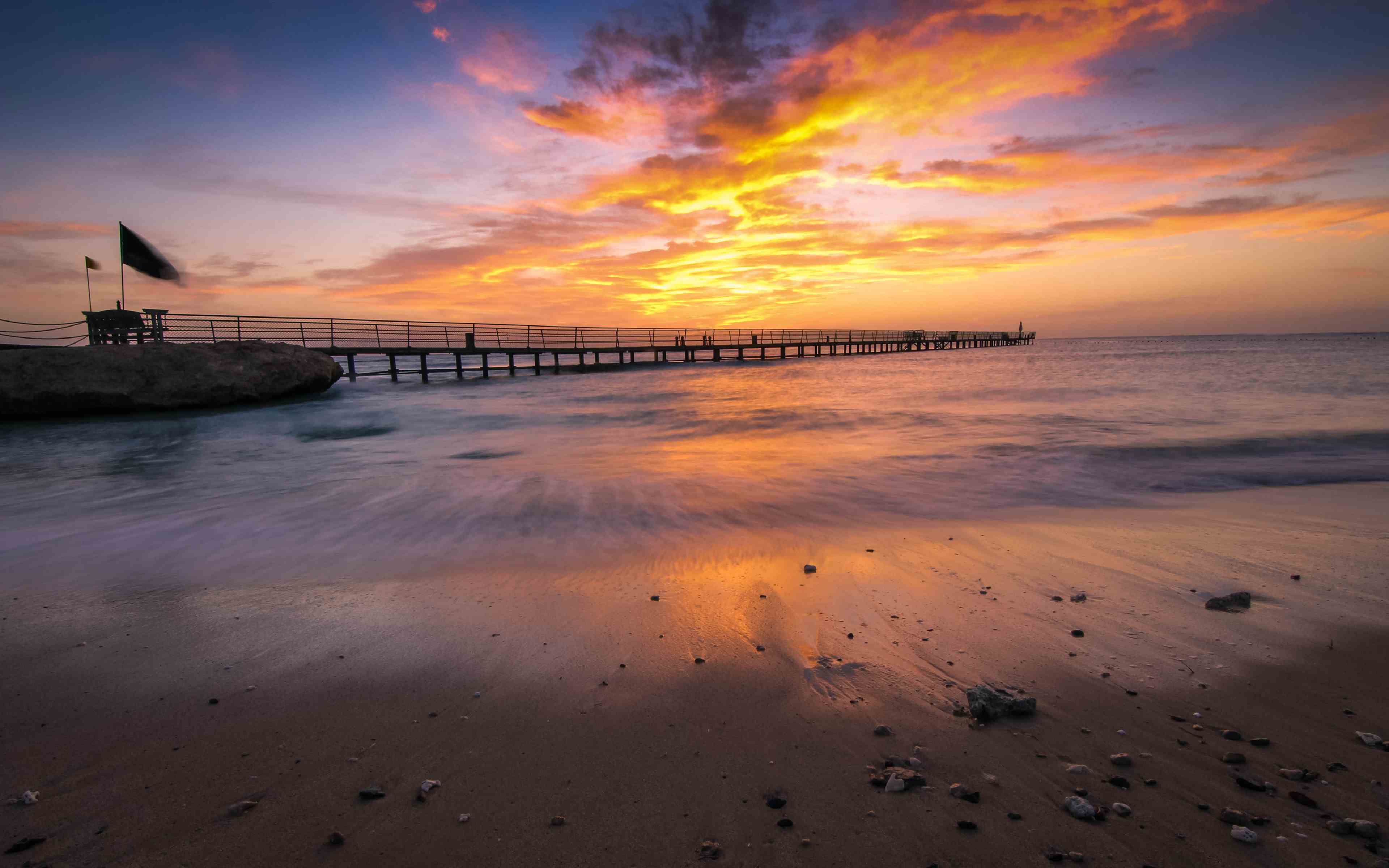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